美麗而蒼涼的手勢 --- 小談張愛玲 (1) —— 陳耀成 1983 年 10 月 號 外

約兩年前,一位《號外》的美國讀者在彼邦發現 —— 一篇張愛玲的英文短文,刊於一本世界作家大全一類的書裏。影印下來,寄給《號外》,又輾轉傳至我手中。我當時看到,相信是一篇極重要的文獻,而記憶中仿佛沒有任何一位張愛玲學者曾經提及,遂把文章中譯,原稿給某半月刊,結果不但沒有刊出,原稿也下落不明。一擱至今,《號外》諸公約稿談張愛玲了,我感到有再譯出的必要,遂再厚顏執筆。並非斗胆在中英互譯隨心所欲的張女士面前班門弄斧,而只希望為自己尊崇的一位作家當一次跑腿,打點一些雜務,該文如下:

張愛玲與父親張志沂和弟弟子靜合照,母親黃素瓊
「我於出生地上海渡過許多年。父母的一場盲婚以離婚告終,我父親是位『風流名士』,母親是位畫家,長年旅居歐洲,然而他倆都相信早年的中文古典教育對我有益,所以自七歲開始,我就受私塾督導。後來我進了一所聖公會女子中學讀了六年,在那裏我發現我的家庭,要不是更極端的話,與當時大部份的家庭並沒有多大分別,中國的大家庭制度要崩潰了,主要藉一些經濟因素而苟且維繫著。我不管父親的反對要往倫敦大學讀書,然而因二次大戰母親把我送至香港大學。大學三年級時,太平洋戰事爆發,我就回到上海,寫小說及電影劇本維生。我愈來愈關注中國的情況,是於共產黨掌政後三年,我才下決心離開。

到香港後我撰寫我第一本的英文小說『秧歌』。此書後來在美國出版。過去居美的十年裏,我主要的工作是翻譯、編電影及播音劇本。我寫了兩本無出版社問津的小說,現時又正在寫第三本。此處的出版社似乎都一致認定,我那兩本刻劃四九年以前中國人生活底小說裏的人物太不可愛,連窮人也好不了多少。諾夫出版社(Knopf)的一位編輯來信說:『要是以往的景況真那麼壞,共產主義就真是一宗解脫。」在這兒我遇上了一種奇異的文學習尚,就是把中國描寫為一個遍地滿口之乎者也的儒家學者底國度,委實是現代文學中的異數。相應而來的是當前對中國看法的二元論 —— 仿佛也就是同一的這些儒家學者給訓練有素的共產黨員統治。然而那裏有的只是腐爛與虛空,和一份對信仰的需求。於儒家思想內在潰敗的最後的日子裏,部份的中國人為於物質主義的虛無主義中尋出路而選擇了共產主義,對其他更多的人來說,共產主義也比回復舊觀較有興味,因為那只不過把家庭以更大的血親 —— 國家 —— 來取代,而這包容了民族主義 —— 我們時代最不容爭議的宗教。我最關懷的却是那夾縫中的數十年。那傾頹、擾攘、充滿最後的憤懑及不安的個人主義底年代。較之往者的數千年或未來的無數世紀真是可悲的短促。然而任何未來的轉變都不能肇自那些中國人淺嚐自由的日子,因為中國並不單只因美國的封鎖政策而與外界隔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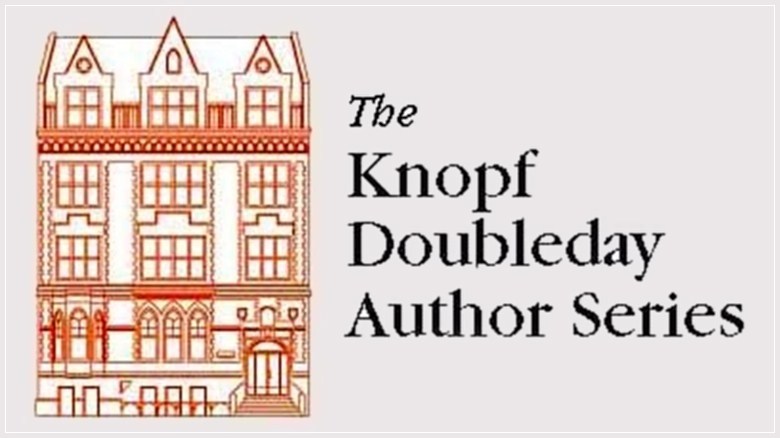
2008 年 Knopf 和 Doubleday 兩間出版社合併
中國比印度、非洲及其他東南亞國家更早就領略到家庭制度於政治結構中起的腐敗作用。現時的趨勢是西方採取一套寬容,甚至尊敬的態度而不深究這制度內的痛苦。然而那却是中國新文學不遺餘力地探索的領域。對『吃人禮教』的不竭的攻擊已有點走過了頭,像鞭撻一匹死馬。反過來,一個惡毒的淫婦又會被表呈為一位抵抗環境壓力的叛徒,把佛洛依德心理學安插至東方排場中。但寫實的傳統持續著,因國恥而生的自鄙而變得更鋒利。相形之下,西方的反英雄還不免有點『三底門答爾』(sentimental) 。我自己因受舊小說的影響較深而不大自覺新文學於我的心理背景上有多大比重,直至我迫於無奈去理論化與解釋,因為我遇上了障碍,確切得如言語不通的障碍。」
張愛玲於1955年賦美,文中提及她旅美十年,所以此文應大約寫於1965年,然而滄海桑田,今日中國於世界外交上的地位已有不同。美國的封鎖政策已給乒乓外交打破,而國內大規模的民主活動有76年的天安門事件。近年西方出現的有關中國的重要報導計有《中國的陰影》、《天讎》、《尹縣長》、《苦海餘生》、《革命之子》等,《秧歌》似乎已遭湮沒。外人對中國政制下的疾苦可能不再「尊敬」了,但瞭解深了多少?面對核子軍備競賽的今天,西方人急欲遺忘的還有二次大戰中最黑暗的一頁:集中營的誕生。猶太人幾要滅族的大屠殺。那有餘暇去深究中華民族的苦難,返顧昔時帝國主義的禍害?

然而時移勢易却不等於張愛玲這文章的中心關注已經過時。從古文化的傾覆,殖民主義的退翳,中產階級底誕生,到共產主義的勃興,張愛玲關懷的年代裏蠢動流佈着互相傾軋的意識形態,她懷抱的當然是一個邈遠而永不能兗現的文化理想。「文官執筆安天下,武將上馬定乾坤」只能是申曲裏的套語。而她最近的長散文〈談吃與畫餅充飢〉是她的往「食」追憶錄,因為「盛筵難再」,因為「享慣口福的中國人,離了本上,都是中國人的災區,赤地千里。」赤地!歷史的,政治的,還是個人的?
未 完 …… 代 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