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at's Wrong With Him
Mimi 打電話來叫我去留英留美同學聯合舞會,叫我和鄭祖蔭一道去。
「Mimi,我不明白你還要留在香港做什麼? Why don’t you justgo back to the States and have babies!」
我不等她回答就馬上收線,這一輪我已經是滿肚子氣無處發洩,她還要在我面前提起鄭祖蔭!
自從 Mimi 告訴我她見到鄭祖蔭不明不白地在觀塘流連之後,我感到又生氣又害怕,我恨我自己對他的認識竟是如此膚淺,完全不知道他真的是個心理有問題的人,所以有次鄭祖蔭打電話來約我打網球,我也本能地一口拒絕了,當然事後後悔是少不免的,但我心怯,叫我怎辦?
終於,我忍不住,找阿 Jan 來研究整件事情,不出我所料,她果然問我:「你有和他很 intimate 嗎?」
「To be very frank,冇。有時在公眾場所他會拖住我的手,或者攬住我的腰,又或者輕輕吻我的面,但這些只不過是基本的社交禮儀,沒有什麼大不了。」
「OK,」Jan 又開始運用她的 expertise 了,「如果要進一步知道他是一個怎樣的人,你一定要同他有更親密的接觸,然後才能親身感覺到他究竟是什麼回事,一個人的心理是否正常,可以從 sex 的態度中表現出來。」
「但他從來都沒有些什麼要求 ……」
「Then he does have problems,你有沒有想過他可能是性無能?」
Jan 對性的確比我們任何一個都開放得多,至少她什麼都講得出口。
「Mary,why don't you make the first move?我們都已經廿幾歲,你又不是第一次,怎不直截了當引他上床去解開你心中的疑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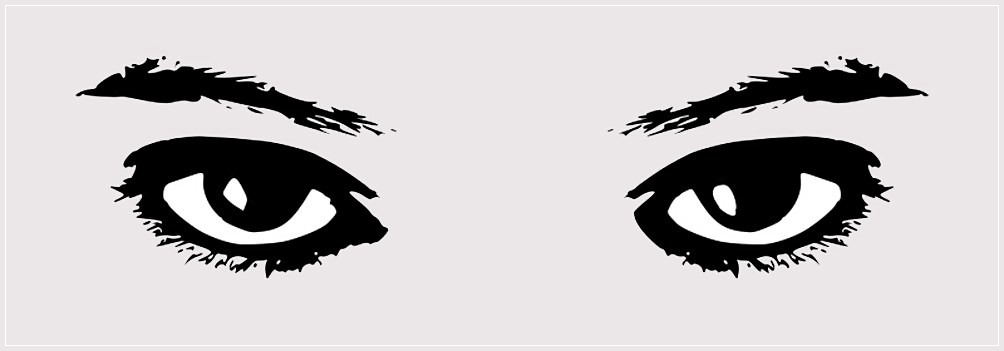
Jan 講到引誘男人好像食支煙那末簡單。
「但 Jan,I was not trained to do such things,你叫我如何去主動?」老實說,我確是很想從 Jan 的身上找靈感。
Jan 作了一個蠱惑的笑容向我說:「Just use your imagination,my dear,你會知道應該怎樣下手的。」
也許 Jan 說得對,我應該徹底解決我和鄭祖蔭的事,現在我需要的是一個下手的機會。
想不到我根本毋須操心,這機會竟由鄭祖蔭親自提供給我!
星期天早上他打電話來,約我下午跟他坐遊艇出海兜風,我問他還有些什麼人同去。
他好像呆了一下,然後輕聲說:「你要有一大班人才肯去?」
嘿!原來他單獨約我出海!So that's it!今次我一定要把事情搞個水落石出,弄清楚鄭祖蔭究竟想點。
我們去到西貢上船時,天下著毛毛雨,我暗中叫好,不是麼,只要下雨,我們在船上的活動範圍便會縮小,到時我死都要他表態!

未到西貢前的白沙灣
鄭祖蔭穿了一條米色短褲、白色厚身長袖 T 恤,夏天的古銅色竟然仍在他的皮膚上留下痕跡,鬈曲的頭髮在戶外顯得特別漆黑。他興致勃勃、很用心地和我講等一會船停時釣魚的種種事情,好像我對釣魚很有興趣似的,看見他的投入和真摯,我忽然感到很內疚,我覺得他好像一隻快要入屠房的小牛,茫然不知我所設下的圈套。其實我們現在相處得多快樂,為什麼我硬要騷擾我們之間和諧的關係?我知道我一搞,we'll never be the same again,但我能忘記他無端端在觀塘穿著 jogging suit 嗎?不,我不能再拖下去。我把心一橫,決定繼續我的計劃。

出到海中,天氣變得愈來愈冷,於是我們走入船艙避風,兩個人坐在小床上喝紅酒,我知道現在就是時候了,我應該有所行動,but,what? how?
不知那裡來的勇氣,我居然大膽起來,慢慢用手除去他的 Ray Ban 黑眼鏡,他那對好像蘊藏著無限心事、無數秘密的眼睛竟不敢望我,他面頰上有三粒小痣,我的手指輕輕逐粒滑過,一直滑到他頸上的喉核。
Ray Ban 最經典的 Aviator 款
我們都沒有出聲。
不要問我誰做主動,總之,somehow 我們擁抱在一起,當時我的心充滿了喜悅,但又不是事先想像般緊張和驚奇,好像一切都來得那末自然、理所當然。
但不久,我開始察覺到有點不對勁,我不止一次暗示想轉換一下我們擁抱的姿勢,而他竟然無動於中,只是緊緊將他的頭側伏在我的肩上,令我看不到他的表情。
突然我覺得我擁抱住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人,我對他毫無認識,他的腦海究竟正在想些什麼?他連我的嘴也不親,像條死魚般伏在我肩上,算是什麼意思?我忍不住偷偷看他的面,發覺他的眼睛緊閉,面上流露出淒然、無助的表情,呼吸變得很急促,身上一起一伏,好像在哭泣的樣子,把我嚇得半死。
但很奇怪,看見他楚楚可憐的表情,我又好像受到感染,有點害怕,谷氣之餘,竟滲入了一絲同情,覺得自己有責任去呵護和安慰他。
不知過了多久,最後我在他的面頰上吻一下,然後輕輕推開他,提議他去準備釣魚的東西。
接著一切都回復正常,沒有些什麼驚人的事發生,大家更沒有提起剛才的一切。鄭祖蔭表現得很安詳自若,又沒有不好意思,而我也出奇地感到滿意。他送我回家時還輕輕吻了我面一下,跟著自己又笑起來,好像是充滿著開心、抱歉、自嘲和安慰的笑。I like that。
本來今日發生的事,我應該大叫 shit,跟著立刻打電話給Jan向她訴苦。不過今次我沒有這樣做,鄭祖蔭可能真是有點不妥,但我忽然又不介意了,而且顯然雖然我不怎樣明白,我總覺得今天我的確幫助到他,令到他快樂了一點。
我願意繼續令他快樂,也許我不需要再去打探什麼,he's entitled to his secrets,就讓我尊重他的秘密吧。
上一篇:D-10 不尋常的事
下一篇:D-12 我決定打這場仗
